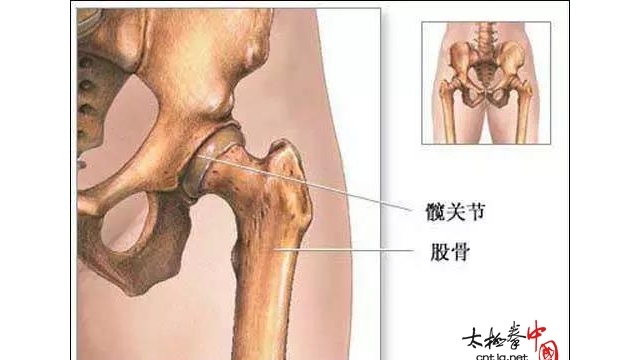不管这个侠怎么变化,他们都会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比如佛教的、道教的、儒家的,我们心目中的大侠不可能完全脱离了中华文化传统而孤立存在于世上。
不管这个侠怎么变化,他们都会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比如佛教的、道教的、儒家的,我们心目中的大侠不可能完全脱离了中华文化传统而孤立存在于世上。
去年梁羽生回港出席天地图书出版公司30周年庆典时意外中风,让众多梁迷牵念至今。
他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陈秉达疗养院接受康复疗养,状况稳定,但是许多在澳大利亚的梁迷仍然专程前往该疗养院,探望病中的梁羽生,令梁羽生很是欣慰。
梁羽生兴致很高,和他们谈诗词曲赋,记忆力一点都未见衰退,他从手边拿过一本《唐宋词选》,说:“这部书中的诗词,我大部分都可以背下来。你们随便翻开任何一页,讲出词牌名,我试试背诵给你们听。”一试,丝毫不差,一字不漏,大家不禁纷纷点头,梁先生的国学根基确实了得。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古典韵味一直为人称道。细究起来,他是国学大师饶宗颐的弟子,而且家学渊源,从小就对古典文学耳濡目染,谈起古诗词自然是头头是道。
从《龙虎斗京华》开创中国新派武侠小说开始,1954年到1984年,30年间,35部小说,160册,1000万字的刀光剑影。《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风靡港澳台和大陆。只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梁羽生,现在已是84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老者。他说自己其实不过是一介书生,并不怎么懂得什么武功绝学,如果说真有什么本领能拿出来“对阵厮杀”的,那恐怕还得说是象棋和围棋。他不仅棋评、棋话写得率性精彩,而且据说可以同时应付几个人,棋力可见一斑。
这些棋评和棋话现在大多收入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梁羽生随笔集《笔花六照》中,梁羽生谈自己入行的经历,谈自己的武侠观,追忆与诸名士大家的往来故事,写陈寅恪、饶宗颐、简又文、金应熙、舒巷城、聂绀弩、黄苗子等文人的风骨,张季鸾、胡政之、金庸、徐铸成、杜运燮、陈凡等报人的风雅,也都能在平淡之中见真情。
汲取中西文学的营养
记者:早在抗战的时候,您和饶宗颐先生就认识了?
梁羽生:是。我原籍广西蒙山县,抗战快结束时,1945年,一批学者来到蒙山避难,其中除了饶宗颐先生外,还有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都住在我家里。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得着这个机会向先生讨教一些文史诗词方面的问题,受益匪浅。饶宗颐先生是国学大师,他在敦煌学方面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
记者:您常常在小说中填词作诗,古典文学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梁羽生:家学渊源让我对于写诗填词有着某种偏好。我从小就酷爱中国古典文史,我写小说,也读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但还是中国古典文学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我的第一本小说《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上连载的时候,故事还没有想清楚,一首词先浮上心头,就拿这首调寄《踏莎行》作为我的“开篇”: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对于文学,我多少还有些发言权,但是对于武术,我其实并不在行,特别是兵器,一开始我可以说完全是个门外汉。不过文学也能帮我一些忙,由于我完全不懂技击之术,我就只能从古人的诗词歌赋之中寻找灵感“自创新招”。比如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来形容长剑上刺和剑圈运转;还有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来描写剑意,也是属于变通之术,以文字的想象空间来弥补我技击方面知识的不足。
记者:您原名陈文统,据说“梁羽生”这个笔名中的“羽”字是因为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所以才取的,《十二金钱镖》的作者宫白羽对您也影响很大吧?
梁羽生:是的。我早期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也着实模仿了一些白羽的笔法。40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我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我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们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食。
白羽是写实派,对人情世故,必定着力描写,所以读他的小说,不会读到什么怪力乱神,绝不会有像平江不肖生写《江湖奇侠传》之奇。50年代,我也受到内地文学风气的一些影响,偏重于写实。《龙虎斗京华》等早期几部小说,多是白羽的调子多一些。但是后来,我就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为什么呢?白羽遭际坎坷,做过许多份工作,生活在底层,所以他能接触到各色人等。可是我家是书香门第,这方面实在是有些缺失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多一些浪漫的想象,但白羽一直是我最欣赏的武侠小说家之一。
记者:新派武侠小说之新,就在于它们脱离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窠臼,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心理描写、叙事布局,其中以古龙最为突出,西方文学对您是否也有启发?
梁羽生:《牛虻》对我写《七剑下天山》有影响,有一天,一个署名“柳青”的读者给我写信,说《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是牛虻的化身,所以他担心凌未风会像牛虻一样在小说结尾处英勇牺牲,因为他太喜欢凌未风了,所以他不希望他死,希望我能改变他的结局。
他的眼光很厉害。我写完《草莽龙蛇传》之后,正好读到爱尔兰女作家伏契克的小说《牛虻》,我被这部小说深深打动。有一天,突然,我想,我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在《七剑下天山》中,我把牛虻分成了两半,牛虻是个私生子,女主角易兰珠是私生女,凌未风则是个反清志士,有着与牛虻相类似的政治身份。
除了《七剑》,像《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都有西方小说的影子,但整体而言,中国古典小说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
三剑楼的三位侠客
记者:怎么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的?
梁羽生:1954年1月,香港发生太极拳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门掌门人陈克夫比武之事,两位拳师互不服气,先是在报纸上登文章打笔仗,后来伤了肝火,就正式在澳门设了擂台一决高低。当时虽然大的世界格局战乱频仍,但港澳地区还算比较“静态”,所以一出现这样火爆的新闻自然是吸引了大众的目光。那天《新晚报》的标题为“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结果却让这些看客大失所望。也许是功夫实力太过悬殊,只打了几分钟,吴公仪一拳把陈克夫鼻子打出血来,陈克夫认输,吵闹了多日的擂台比武就此草草结束。
虽然结局不太让人过瘾,但大家对于武术武侠的热情却水涨船高。《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见机会难得,就来对我说,平时你就喜欢和朋友大谈武侠故事,不如乘此热潮来写一个连载。我一开始说不行不行。虽然我喜欢读武侠小说,但我当时总是觉得写武侠小说即使能够成名,也并非正途。而且我是《大公报》的社评委员兼《新晚报》副刊编辑,还写着两个专栏,都挺受欢迎。我并不是特别想写,但罗孚情真意切,我实在推不掉,才勉强答应了,硬着头皮上。本来说还要再考虑一下,结果第二天就看到报纸上写了预告,说我的小说第二天可以与读者见面。没有办法,只能写,没想到就此获得了成功。
记者: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其实就是您所写的,您说:“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您是否觉得金庸先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更大一些?
梁羽生:我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小一些,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所以写此类小说者,往往不能脱离于前人之框架,为复仇、探秘、斗法、比武等故事所左右,无法出新。
我觉得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金庸先生。金庸开始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只比我晚一年,这部小说脱胎于民间关于乾隆的故事传说。金庸的家在浙江海宁,所以从小就对此故事耳濡目染,写来自然如鱼得水。但那部小说还是章回小说的结构,到了第二、第三部小说之后,他的小说更是走向了一条新途。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善于吸收西方文化,特别是写作的技巧。《碧血剑》中已经明显有西方电影的手法,而他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中则越来越深入地着重于人性的刻画,梅超风、东邪黄药师、江南七怪都是亦正亦邪的人物,这就突破了侠与盗之间的正反面形象的模式,把武侠小说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记者:您、金庸、百剑堂主曾经合写过一部散文随笔集叫《三剑楼随笔》,如今百剑堂主已经去世,您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
梁羽生:百剑堂主原名陈凡,50年代中期写过武侠小说,叫《风虎云龙传》。他于1997年9月去世,一晃10年过去了。当时我写过一副挽联:“三剑楼见证平坐,亦狂亦侠真名士;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写《三剑楼随笔》时我们都在《大公报》任职,他是副总编辑,我和金庸是副刊编辑。陈凡当过记者,身上有“侠气”。抗战期间翻过广西十万大山,沿中越国境边界线采访,写下了《中越边境见闻》系列报道,又报道过1944年夏秋之间湘桂大撤退时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他从不隐瞒事实,总是仗义执言,曾敏之说他“不问虚名值几钱,只凭肝胆看幽燕”,是没有夸大的。
他觉得我们三人都写武侠小说,不如合开个专栏,名称就叫“三剑楼随笔”。从1956年10月开始,一共只维系了3个月的时间,不过却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共计15万字,这也是我们友谊的见证。
记者:我读《三剑楼随笔》的时候就对您写的棋话特别感兴趣,写得惊心动魄,您是不是特别喜欢下棋?
梁羽生:我和金庸都特别喜欢下棋,围棋和象棋都喜欢。我们写《三剑楼随笔》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比较关注棋坛方面的动态,并将各种逸事写成随笔。
我当时还曾经编过《大公报》的象棋专栏,在这个专栏里,象棋一代宗师杨官璘发表了他的《棋国争雄录》,我也写过围棋和象棋的评论。我还曾以《新晚报》象棋记者的名义,采访过重大的赛事,像全国棋赛和亚洲棋赛我都做过报道,亲眼看到棋坛厮杀,回来就写成报道或专栏随笔,慢慢地也积累了不少文章。
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记者:1977年,您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上讲《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提出了“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观点,但侠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也有不同看法的?
梁羽生:我是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观点的,武侠小说不能只注意渲染刺激的武打场面。但武侠小说毕竟是武侠小说,它也没办法脱离开武术去。倘若因此就认为武侠小说低人一等,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保守的陈见。现在好多了,以前不要说在大陆,就是在香港,也很少有大报会连载武侠小说,大报不太看得起武侠小说。
侠的内容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几乎每一个武侠作者心中就有一个侠的概念,从古人对于侠的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有的主张要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有的认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侠的行为”,有的认为只要是人类某些高贵品质的表现就是侠。但不管这个侠怎么变化,他们都会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比如佛教的、道教的、儒家的,我们心目中的大侠不可能完全脱离了中华文化传统而孤立存在于世上。
记者:您对改编自您的小说的香港武侠片怎么看?
梁羽生:武侠片和武侠小说一样,也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我的小说也被多次搬上银幕。《少林寺》的导演张鑫炎也是我的小说《云海玉弓缘》、《侠骨丹心》和《白发魔女传》的导演,他和我合作多次,大家也颇有默契,成绩也很喜人。
《白发魔女传》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小说,后来于仁泰导演和张国荣、林青霞合作的那一版影响也很大,在巴黎影展上还得过奖。它先后被改编成国语、粤语电影以及长达40集的电视片集。
第一个“白发魔女”是1957年峨嵋公司的罗艳卿,这是粤语影片,卖座很好,所以她就连演了三部。第二个是佳视制作的李丽丽,鲍起静、蔡少芬也演过白发魔女。
徐克导的《七剑下天山》我也看了,意识流,很有意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曹凌志先生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致谢。)